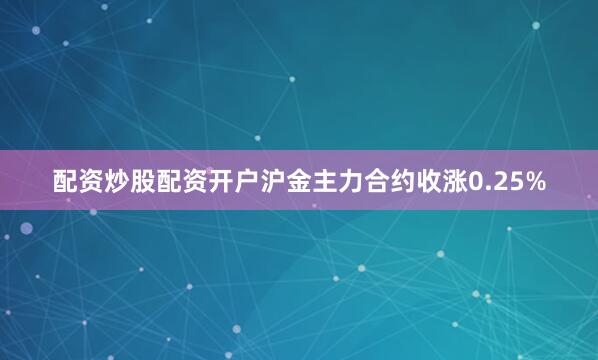文|云初
编辑|云初
文|云初
编辑|云初
那天,济南党家庄,雾很大,山很静。
一架飞机从天空穿过,低得不寻常。几秒后,撞山、爆炸、燃烧。巨响掀翻山头的清晨,也掀翻了一个时代。
徐志摩死了,年仅三十四岁。他不是普通旅客,是那个写下《再别康桥》的天才诗人,是新月派的灵魂人物,是民国知识界的风流代表。
可他死得并不“诗意”。头部有洞,全身骨折。火没有把他烧焦,撞击先让他遍体鳞伤。
他的死引发太多传说,太多疑问。飞机坠毁,他是意外还是劫数?追悼会上,遗体重殓,他是体面还是破碎?几十年后,墓地被盗,他是否还能安息?
让我们回到那一天,1931年11月19日,民国二十年,一个注定被载入文学史和死亡史的日子。
徐志摩死了,年仅三十四岁。他不是普通旅客,是那个写下《再别康桥》的天才诗人,是新月派的灵魂人物,是民国知识界的风流代表。
可他死得并不“诗意”。头部有洞,全身骨折。火没有把他烧焦,撞击先让他遍体鳞伤。
他的死引发太多传说,太多疑问。飞机坠毁,他是意外还是劫数?追悼会上,遗体重殓,他是体面还是破碎?几十年后,墓地被盗,他是否还能安息?
展开剩余84%让我们回到那一天,1931年11月19日,民国二十年,一个注定被载入文学史和死亡史的日子。
那天早晨,徐志摩从南京起飞,搭乘的是中国航空公司的“济南号”双翼邮政飞机。天气预报说北方有雾,他没在意。他在赶时间,要飞北京,去听林徽因的讲座。
南苑机场那头,林徽因和梁思成已等候多时。风刮过候机坪,没看到飞机,只见云低压城。林心里发紧,梁在查看时间。
上午8点出发,原计划10点前抵达。但9点刚过,山东济南党家庄的村民听到异响。一架银色飞机穿雾而来,像醉酒鸟般摇晃。它贴着山头,突然砰地一声——撞山。剧烈爆炸,机身断裂,火光冲天。
没有呼救声,没有挣扎,只有碎片和烟雾飘散。
几个村民赶到现场,看见焦土中三具尸体:飞行员、报务员、旅客。尸体残破不堪,尤其是徐志摩,穿着深色马褂,帽子还在,面部却被硬物击穿,头部开了个大洞,血肉模糊。
他不是被烧死,而是被撞击当场致命。根据当时警员记录:他的腿部骨折严重,肋骨断裂,全身多处扭曲,尸体像被钢爪挤压过。
下午3点,南苑机场的地勤通知“济南号失联”,林徽因当场变脸,梁思成立刻联系济南警署。傍晚消息确认,飞机坠毁于党家庄,乘客无人生还。
噩耗传回上海,北平震动。媒体次日头版大字标题:“诗人徐志摩殒命空难!”
那个崇尚飞翔的诗人,死于飞行。
遗体修复与重殓矛盾
遗体暂厝济南福缘庵。庙宇幽静,香火残留。灵堂草草搭起,寒风灌入,香烛摇曳,徐志摩的棺椁搁置正中,周围围满了人——济南地方官、朋友代表,还有远道赶来的家属。
陆小曼没有第一时间抵达。据说她接到电报时拒绝相信,反复念着:“他不是说只飞两个小时吗?”
数日后,她终于到济南,在灵柩前站了很久。她没哭,只盯着那口棺。外人看不出她是崩溃还是麻木。灵堂静极了,香灰落地声都能听见。
灵柩开启前,随行医者曾提醒:“头部撞伤严重,遗容难辨。”但为了安葬体面,家属坚持修复。
福缘庵里悄悄开始“重殓”。
棺中之人,头戴瓜皮帽,帽下是缝合过的裂痕。面部一侧塌陷,眼眶内陷,用纱布填补。马褂掩盖的是碎裂的肋骨和塌陷的胸腔。技师说:“只能做成远观可看,近看仍惊。”
这种“重殓”,在民国追悼中极罕见。它象征一种“修复死亡”的努力,也是一种压抑的哀悼方式。
灵堂布设朴素,黑白横幅写着“魂兮归来”,门前松柏掩映,纸幡随风飘扬。送行者中,有北大同僚,有文友学者,还有他旧识梁思成。
而徐志摩,那具身体,已不是“诗人”,而是“遗体”——骨折、破损、缝合、穿衣。
灵车出发前,有人提议就地安葬。但家属否决。他的灵魂属于江南,要回上海,要回海宁。
于是,11月21日下午,灵柩由火车护送至上海。沿途车站设简易停靠,有人献花,有人驻足,有人念起《再别康桥》。
死去的,不只是一个人,还有那个浪漫理想主义的民国青春。
上海追悼与海宁入葬
十一月下旬,上海正值深秋。徐志摩的灵柩搭乘专列,从北方一路南下,停靠数站,最终抵达上海北站。车厢外,人群围观,铁轨旁已是黑白挽幛,墨迹未干。
灵车缓缓驶入万国殡仪馆。那是上海当时最具规格的悼念场所,玻璃屋顶、铺着红绒地毯的追思厅,摆满白色花圈和哀挽旗。徐志摩的照片被放大,挂于厅正中央,他那招牌微笑,如今竟显得空洞。
遗体送入整容室,进行第二次“重殓”。由于此前撞击伤重,加之长时间运输,尸体已有明显僵直,必须再次缝合、整理。整容师封闭瞳孔,缝补颧骨,将深陷面容尽力复原。
马褂换成白绸寿衣,帽子仍戴,领口以白布束紧。面对舆论和仪式要求,这具残缺遗体被修复成“体面诗人”的模样。
11月24日,追悼会正式举行。静安寺内黑纱低垂,殿堂中央置放灵位,香烟袅袅,钟声沉沉。宾客云集,胡适、林语堂、金岳霖、郁达夫、陆小曼等文化名流皆到场。
悼词一篇篇念出,有的理性、有的激昂、有的哽咽。胡适题字墓碑:“志摩之墓”,同时在悼词中称其“真诚自由,清新俊逸”。
但最受关注的不是话语,而是目光交汇——林徽因与陆小曼分处左右,身着素衣,低头不语。一个是曾经的缪斯,一个是最后的妻子,两人眼神未曾接触,却同样苍白。
马褂换成白绸寿衣,帽子仍戴,领口以白布束紧。面对舆论和仪式要求,这具残缺遗体被修复成“体面诗人”的模样。
11月24日,追悼会正式举行。静安寺内黑纱低垂,殿堂中央置放灵位,香烟袅袅,钟声沉沉。宾客云集,胡适、林语堂、金岳霖、郁达夫、陆小曼等文化名流皆到场。
悼词一篇篇念出,有的理性、有的激昂、有的哽咽。胡适题字墓碑:“志摩之墓”,同时在悼词中称其“真诚自由,清新俊逸”。
但最受关注的不是话语,而是目光交汇——林徽因与陆小曼分处左右,身着素衣,低头不语。一个是曾经的缪斯,一个是最后的妻子,两人眼神未曾接触,却同样苍白。
当晚,遗体未立即入土,而是暂存于棺内,等待海宁家族的决定。沪上民众纷纷赶来吊唁,殡仪馆外,排队长达数百米。不少人念起《偶然》《再别康桥》,低声吟诵,在风中留下一段段私人的送别。
徐志摩的身体终于安静了。他的声音却开始从无数人口中流传。他已不再是个人,而是一个时代的“象征”。
1932年初春,天气回暖,灵柩随家人护送回浙江海宁。长途车队在青山绿水间穿行,抵达东山万石窝,山脚下早已挖好墓穴。墓址选在西山背面,依山而建,风水格局讲究“前有水,后靠山”。
石碑由胡适亲题,正中镌刻“志摩之墓”,下有两行小字,记其生卒年月及挽联。墓前用青砖铺路,左右种植松柏,寓意长青。
落葬那日,风中携着余雪。家族不设哀乐,只鸣鞭送行,棺木缓缓下葬,封土齐整,一锹一锹,直到墓穴被完全遮盖。
他终于回到了南方,也终于回到了大地。
盗墓、重修与纪念
时间来到三十余年后。
1966年秋天,“文化大革命”掀起全国风暴,浙江海宁也未能幸免。红卫兵抄书、砸庙,最终盯上了墓地。徐志摩墓,因其“资产阶级情调”、因其诗人身份,成了清理目标。
一纸红头文件下达:“破四旧”,连带执行。
徐志摩墓地被推倒,碑被砸毁,尸骨被掘出。下葬多年的棺木被撬开,尸骨已然风化。有人说头骨仍在,有人说散落无存。随葬物品,包括书信、笔筒、布履,全数失踪。
原址被改为化肥厂废地,仅余断柱几根,杂草覆盖,再无人知此地何名。
文学界缄口不言,亲属无人问津。徐志摩从“民国偶像”变为“时代尘埃”,在官方记录中消失近二十年。
直到1983年,浙江海宁市文化局发起“修复文物”提案。在多方推动下,重修“徐志摩墓”工程开始。
旧址已不可寻,地方政府选址西山公园,在原墓地西侧三十米重建新墓。保留胡适旧碑,围以白石栏杆,新墓呈“书卷形”地台,寓意“文以传人”。
墓园中央设有雕塑区,立有徐志摩头像浮雕、诗碑墙,以及三件雕刻艺术品:柳影、康桥、羽翼——分别对应其代表作《再别康桥》《翅膀》等象征元素。
纪念馆内收录生平、诗稿、手迹、信函,陆小曼书信残片亦存,林徽因题词也得以展出。
今日的徐志摩墓,已成为国家级纪念园,每年接待游客数十万。青少年在诗碑前吟诵“轻轻的我走了”,摄影师在柳影中拍下倒影,人们在雨后留影,“民国气息”成了一种审美潮流。
可无人记得,那年飞机撞山,他是如何扭曲着死去;那口棺木,在福缘庵如何被缝补、翻整;那具尸骨,如何在夜晚被扔进荒草。
诗人死了不止一次。
第一次,是1931年11月19日,党家庄山头;第二次,是1966年秋天,铲子撬开棺木时;第三次,是当他的诗被抄成网红滤镜、当墓碑成了自拍背景时。
他已经从“人”变成“纪念品”。
但也许,他不在意。毕竟他曾写下:“我不是归人,是个过客。”哪怕连墓,也只是“借住”。
发布于:北京市股市杠杆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a股怎么加杠杆”智能化改造:数据自动采集
- 下一篇:怎么配资发布于:北京市